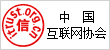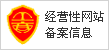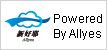伏特加与俄罗斯的爱恨情仇
俄罗斯人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俄罗斯人并不认为在上帝创世之前天地是一片混沌,至少混沌中还有伏特加。在辽阔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一切全源于伏特加,一切全归于伏特加。
二十世纪初,俄军官兵能够完成艰苦的训练,惟一的支柱就是斯米尔诺夫(Smirnov)牌的伏特加。与此同时,伏特加给这个国度带来的伤害却大过了任何一次战争。在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十年间,共有14000名士兵死亡,但每年俄罗斯却有三万多人死于酒精中毒。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每年能喝下比俄罗斯还多的酒: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5公斤白酒,其中至少一半是伏特加。
伏特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共同点是,二者都给无数俄罗斯家庭带来了伤痛。伏特加这个词儿一旦被人提起,就会引发出无法预料的行为。有傻笑的,有不停打响指的,有自己跟自己掐的,有闷不吭声的,什么都有可能,惟一不可能的是独醉。不管在哪一种政治制度下,俄罗斯人永远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质。伏特加能决定俄罗斯人的生和死。伏特加就是俄罗斯的神。2003年,这位大神迎来了它的500岁诞辰。
爱也是它,恨也是它——伏特加把俄罗斯人整疯了!
1970年代初的一天,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从郊外的扎维多沃高官官邸返回莫斯科。那天,给他开车的是苏共总书记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两位领导人共处一车,葛罗米柯觉得现在正合适谈一个比较难弄的话题,于是他说道:“列奥尼德-伊利伊奇,我们得管管伏特加了。人民就要全变成酒疯子了。”
勃列日涅夫没有做声。五分钟后。葛罗米柯正在暗自后悔不该提这事时,勃列日涅夫突然道:“安德烈,俄罗斯人民离了这个什么也做不了。”
这个小段子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讲的,他则是听葛罗米柯亲口说的。每个俄罗斯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的想法与勃列日涅夫相左,戈氏成为了伏特加史上惟一一个下令禁用伏特加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认为,工伤事故增加、生产效率降低、人均寿命缩短、交通事故频发,这些都是伏特加惹的祸。1972年,苏联政治局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做出决议。戈氏说,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因为国家的预算也“喝醉”了,因为预算里面很大比重来自于伏特加的销售收入。用借用伏特加的销售来弥补预算,这本来是斯大林的决定,但只是一个临时决定,结果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伏特加在预算中贡献的数字从1000亿卢布增加到了1700亿卢布。
苏共党内的确不乏醉汉。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喝得酩酊大醉,叶利钦甚至用炫耀自己喝醉过来勾引女人,以显示自己与平民一样。
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刚两个月,便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从此,戈氏拉开了与伏特加的斗争序幕,他相信自己能够获得人们的支持,因为一个对两百家工厂所做的调查显示,工人们虽不赞成禁酒,但都支持对饮酒加以限制。然而,这场禁酒运动最终仍演变成了苏联官僚制度的另一个笑柄。
戈尔巴乔夫关闭了伏特加酒厂,取缔了大部分酒类商店,禁止苏联驻外使馆用酒,甚至还用推土机推倒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库班河流域的葡萄园,这一切无不令酒乡俄罗斯举国嚎啕。后来,戈尔巴乔夫得外号“矿泉水总书记”。
随后,如戈尔巴乔夫所料,丈夫们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多了,生育率自然提高了,人均寿命也延长了。但是,戈氏没想到的是,苏联国内出现了食糖短缺。人们抢购并且储藏食糖,是为了在家里酿酒。更令戈氏想不到的是,竟然有人开始饮用各种有毒的致醉品,比如制动液,俗称刹车油。我还记得在那时看到过的一个商店标牌,那是在伏尔加河北端的一个小镇上,标牌上写:“古龙水,下午2点供应。”
也许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是非常不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市,那里的人都习惯喝红酒,所以他不知道伏特加对人的心理能造成多大的影响。在1980年代,在这个伏特加当货币使时比卢布还要靠得住、70%的凶杀案件是因酗酒而起的国家里,伏特加的力量远远强过了戈尔巴乔夫手中的权力。
最终,可怕的统计数字令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他的禁酒令。尽管戈氏怀疑这些统计数字在政敌那里被故意夸大了,他仍哈哈大笑着给人讲了一个笑话:“人们排起长队买伏特加,有一个人实在忍受不了了,便说:‘我要去克里姆林宫杀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仍在排着长队的人们问他:‘你杀他了?’他回答说:‘杀他?那边排的队比这儿还长!’”
伏特加
伏特加的发明过程很少见诸史籍,不过这个过程倒不见得传奇。俄罗斯人认为伏特加神圣且永恒,不会因历史而改变。
1977年,美国的伏特加酿造公司集体起诉苏联的酒厂,指控后者意图让人们相信美国市场上的本土伏特加是不正宗的,随后引发的商业丑闻则掀起了伏特加历史的研究热潮。
然而,真正威胁了苏联人的却不是此事。同年,同是华约成员国的波兰宣布自己才是伏特加的真正原产地,苏联无权将其生产的白酒命名为“vodka”。紧张的苏联官员立即动身寻找能够重证其为“伏特加之乡”的能人,最后这个重任落在了历史学家波赫列布金的肩上。波赫列布金不负众望,著文论称波兰人始酿伏特加晚于俄人数十年。可叹重振俄国酒威的波赫列布金两年前被杀害在莫斯科南郊的家中,据传系波兰人所为。
根据传说,伏特加最早为十五世纪晚期克里姆林宫楚多夫(Chudov)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所酿。起先,修道士们酿酒所用的酒精要从热那亚进口,后来便逐渐开始采用本地用黑麦、小麦和绵软的山泉水生产的酒精。
这个故事的一切细节都极度充满了象征意义:跟上帝扯上了关系,修道院名也有蕴意(“Chudov”在俄语中意为“奇迹”),背景还是俄国首都。遗憾的是,不少与伏特加的生世有关的文件都毁在了十七世纪中叶俄国东正教教会手里,教会后来宣布伏特加为恶魔的发明。
将酒精与水混合的制酒方法沿袭自地中海文化,尤其是古希腊。古希腊人已开始用红酒与水相混合,不过这种混合物初时更可能是用来处理伤口的消毒水。不久,伏特加就告别了其医用价值,变成了瑞典人记忆里1505年远征莫斯科时见到的一种“烧酒”。十数年后,这种烧酒点燃了所有的俄罗斯人。到了1533年,俄罗斯将伏特加的生产放开给小酒馆业主,从此后,“狂欢”——对于原本只饮蜂蜜酒的俄罗斯人来说本是“酩酊大醉”的代名词——现在已经成为了日常活动。
好景不长。1648年,一场暴动在莫斯科的一家酒馆里爆发,随后蔓延到了其他市镇,危急的情势让当局看到了伏特加泛滥后带来的后果:全国三分之一的男人都欠着酒馆的酒钱,而农民们又因为沉溺酒肆而荒耕数年。于是,俄国政府收回并垄断了伏特加的销售权,这就意味着酿酒商的利润越来越少。从那时起,伏特加就多了一个特征——家庭酿制。
在俄罗斯,伏特加曾六次被禁止。
这一垄断权曾先后六次被撤销(最近一次是被1992年的叶利钦政府撤消),同时也六次被恢复(最近一次恢复则是在1993年叶利钦痛感造酒业罪案频频时),但每次反复最终都只能进一步让人们为伏特加疯狂。
“我为如此嗜酒成性的俄罗斯人民感到难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其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1894年,维特推出了一项旨在提高伏特加质量、同时也巩固了政府垄断地位的计划,俄国化学大师门捷列夫曾经担任过这一计划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伏特加的酿制过程非常简单:一份酒精加一份水,再调入少量其他添加剂以去其辛辣(如斯托利奇那亚牌伏特加里的添加剂是糖)。
支持饮酒的知识分子最爱提的名字也许还不是门捷列夫——尽管他发现了调制伏特加的最佳比例(即酒精比例为40%),而是俄国生理学家尼古拉-沃洛维奇,沃洛维奇的研究认为,每天饮用50克伏特加有强心活血之功。就在民间禁酒组织陆续出现于全国各地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政府再次宣布禁酒。
一战结束后,十月革命爆发,但禁酒令仍未解除,趁着全国一片混乱之时,红军和白军都四处免费“光顾”伏特加酒馆,滥饮一气。波赫列布金在论文中幽默地指出,红军最终赢得了胜利,原因之一便是他们更好地守住了酒馆,并以枪刑来处罚酗酒者。二十年代中期,列宁废止了禁酒令以赢得民心。列宁下令生产“里科夫加”(以当时的苏联财长阿列克谢-里科夫命名),此酒因酒精含量稍低(35%)而较伏特加更为温和。但列宁逝世后,伏特加重又返回人们的生活中,其强劲的销售额也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出了贡献。
苏德战争打响后,苏联国防部规定,前线士兵每天每人能获得100克伏特加的配给。所以苏联的伏特加酒厂一致认为,苏联之所以能打赢纳粹,靠的就是两样:伏特加,以及喀秋莎火箭炮。
到了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家控制酒类生产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整个伏特加酿制业于是乱作一片。与此同时,俄罗斯被“新俄罗斯人”带上了“万恶”的资本主义轨道,而这帮新富当年就是靠着走私伏特加发达起来的。
门捷列夫不仅仅贡献了伏特加的标准配方,甚至连伏特加的名字也是他取的。在他之前的数世纪里,官方文件在提到伏特加时皆称之为“谷酒”。伏特加的别称远不止这一个,到今天为止,伏特加的诨名在数量上仅次于阳具,其叫法有“开水”、“垄断波尔卡”、“泡泡”、“机轴”、“苦玩意”、“白玩意”,最经典的是苏联时期的“半升”、“1/4瓶”和“女娃”。从词源上讲,“vodka”来源于“voda”,后者在俄语中意为“水”。
19世纪中叶,“водка”(vodka)一词开始被收录于标准俄语词典中,但此时的伏特加仍被上流阶层视为没有文化——甚至是粗俗——的象征。伏特加最初的消费者就是底层民众,这只能怪当时用木精酿制的伏特加质量太次,闻起来极像机油,而粗俗的酒馆文化也是一大原因。此外,在19世纪晚期以前,伏特加一直是散装,惟一的计量标准是“vedro”(即桶,一桶伏特加约有12公斤)。
俄罗斯与伏特加之间有着太多的爱恨情仇
伏特加与其他任何种类的白酒都不一样,因为人们从来没有为喝伏特加找到过正当的理由。法国人会赞美科涅克白兰地的芳香,苏格兰人会夸耀威士忌的口感,而伏特加,既无色,又无臭,亦无味,喝起来还很呛。俄罗斯人喝伏特加,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一口灌下去,然后傻笑,然后骂娘,然后四处找人“醒酒”。所以对俄罗斯人来说,把伏特加直接注射到血管里,和喝下去没什么区别。
虽说伏特加天生劣质,但到了后来也算是有了自己的文化。伏特加文化有自己的传统(如“一端杯,杯莫停”),有自己的口号(如“伏特加是红酒的姨娘”),有自己的讲究(在俄罗斯,醉汉是和酒鬼区别对待的,因为前者每天要等到下午五点才开始饮酒),有特制的下酒菜肴(如鱼、腌黄瓜、肉冻、泡菜),当然,还少不了敬酒辞,也就是任何一个值得端起酒杯的共同话题。
伏特加控制了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的意志和意识。除却家庭不幸和街头狂欢,除却幻梦与理想,伏特加带给俄罗斯人的还有无数的自杀、他杀,以及非自杀非他杀的莫名死亡(俄罗斯人闲谈时爱聊的主题包括谁谁谁酒后狂呕时把自个儿噎死了,以及谁谁谁酒醉后一脚踏出大楼的窗户)。然而,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在面对醉酒撒疯时心情都很愉快。过去几个世纪来,这种愉悦感屡屡令外国访客惊讶不已。1676年出使俄国的荷兰外交官巴尔塔萨-柯伊特写道:“我们只看到了浪荡之徒的羞人举止,围观其醉态之众反令其更加放肆。”
三个世纪之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作家维涅狄克特-埃洛费耶夫的笔下,一切仍暗合着柯伊特当年的记录:“俄罗斯每一个有一点点价值的人,每一个对国家有一点点用的人,都在像猪一般狂饮。”
不管戈尔巴乔夫等人能数出伏特加的多少坏处,出生于以喝酒狂放著称的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当代作家叶夫金尼-波波夫仍坚信,在这个不那么完美的国家里,正是伏特加支撑着俄罗斯人民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伏特加提供了一种真正与政治无关的私人空间,一个可以在幻想的自由中得到放松、忘却烦恼、纵情做爱的地方。文学与饮酒,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未像在俄罗斯这样紧密。不管是革命者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还是流亡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也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抑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无不是贪杯之人。波波夫对我说:“伏特加令构思情节更加容易。”
但伏特加不仅仅能壮胆,同时也能令醉者大受自遣和自责的折磨,而这些感受恰恰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特征。所以,喝醉了的俄罗斯人常常会问酒伴的一句话是:“你尊重我吗?”
2003年,一座伏特加博物馆在莫斯科落成,还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来给五百岁的伏特加贺寿。可以说,五百年的伏特加史,就是五百年的控制与反控制史。五百年来,俄国政府一直想要控制人民对伏特加的依赖,而每一次控制都只能令人民对其依赖更深。然而,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这次诞辰五百年庆典有可能成为伏特加的告别仪式。
麻醉品专家弗拉基米尔-努日尼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战争根本就是“反科学”的,而真正可能打赢这一仗的,也许是俄罗斯正在拥抱的资本主义制度。努日尼指出,新一代的俄罗斯企业家已经不饮伏特加,这些年轻人早已改喝啤酒,对他们来说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而在私营企业里,酗酒的员工则会被开除。因此,努日尼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势头好,15至20年的时间就能带来极大的改观。戈尔巴乔夫也说,未来将在啤酒和红酒身上。
伏特加文明正在发生分化。莫斯科的精英们喝的不是进口酒就是高级伏特加。他们饮酒,但从不喝醉。而滴酒不沾也在慢慢地成为一种时尚,主张禁酒的总统普金就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但在广袤的外省,这种转变仍不显著。而在农村地区,伏特加仍然具有代金价值。对那里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做出选择的不是“喝红酒还是喝伏特加”,而是“喝劣质伏特加还是喝自酿的伏特加”,而昂贵的优质伏特加只是一种可以用来显耀的奢侈品。
简而言之,我们的伏特加大神不会轻言放弃,但是它可以被驯服,甚至被放逐到历史的迷思中去。伏特加一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高尔基在自传中写到他在伏尔加河畔度过的童年时说,人们为高兴而喝,人们也为悲伤而喝。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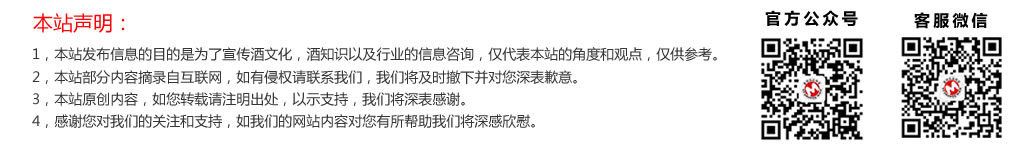 |
| 上一篇: 与茅台酒相关的清代诗歌 |
| 下一篇: “液体黄金”的文化气质 |
- 相关资讯
- 推荐阅读
- 热点资讯
- 江西四大名酒2021/06/01
- 赤水河,养活了中国60%的名酒,为什么被誉为…2021/05/27
-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想说说豫酒2021/05/16
- 中国白酒之都,年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却只是山…2018/12/05
- 中国八大名酒都有什么?是怎么评比的?2018/12/03
- 赤水河,养活了中国60%的名酒,为什么被誉为…2021/05/27
- 中国白酒之都,年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却只是山…2018/12/05
- 爱上红酒,更爱红酒文化,了解红酒养生2018/12/03
- 中国古代酒具的发展2013/12/23
- 从云集酒坊到会稽山绍兴酒2014/07/26
- 武威葡萄酒文化历史探寻2018/12/03
- 和谐共赢的保健酒企文化2014/06/05
猜你喜欢
- 限量版红酒让嘉宾流连2014/06/03
- 茅台袁仁国谈白酒行业要仰望星空:…2014/06/07
- 中国企业为何大而不强2013/08/21
- 品鉴进口酒不再进“雾区”2014/03/11
- 武汉女白领KTV里连飙高音 唱破…2014/05/15
- 酒参展,瓶瓶盖盖跟到来2014/03/24
- 不摆酒返礼金是钻“禁酒令”空子2014/03/14
- 全球最著名的十大“奇葩”葡萄酒2016/11/26
- 食品安全宣传周酒类知识公益宣传活…2014/07/20
- 共享世界杯激情董酒邀你猜冠军2014/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