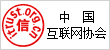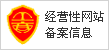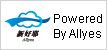白酒品牌“转基因”
2013年伊始,悲观情绪笼罩着白酒行业,一线品牌纷纷加码中低端产品“御寒过冬”,二三线品牌争推小酒防守反击,一时间“亲民”风起云涌。加码中低端也好,争推小酒也罢,还只是“近忧”导致的动作层面的本能反应,战略层面的“远虑”尚未顾及。白酒行业的经营假设系统已发生根本变化,在此背景下,行业的核心命题不再是增长,而是进化;不再是顾盼自雄,而是放下身段,回归“民酒”;不再是长肌肉,而是转基因,特别是站在消费者价值的角度重塑品牌形象。白酒品牌“转基因”,主要关涉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
寻找“湿件”
一个完整的白酒品牌应该有硬件、软件和“湿件”三个部分。硬件是一种物理存在,比如香型、瓶型、标准色等;软件是历史、品牌故事、荣誉等,比如宋河的老子文化、茅台与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老八大名酒的殊荣、国台“通达人生”的品牌口号等。据笔者的观察,每一个白酒品牌都会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但只有少数白酒品牌拥有湿件。
“湿件”概念来自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湿,作为干的反义词,在“干”隐喻机械的、乏味的情况下,“湿”则隐喻人的活性。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中,缺乏女人味的上司爱上了缺乏男人味的下属。女上司不太确信自己对男下属是否有吸引力,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女上司严厉地质问男主角:“你说我干巴巴的?”男主角吓得失了方寸,结结巴巴地说:“不,正相反,你湿呼呼的。”这里的“湿”形容一种有血有肉的魅力。
品牌就是一个“人”,当然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魅力的人,而只有硬件和软件的品牌就难免干巴巴的。一个品牌有湿件,还表示它真正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它把消费者当成一个有情感、有情绪、有人性的优点和缺点的人。洋河蓝色经典的“男人的情怀”就是湿件,与天下男人心照不宣,有点“自来熟”的味道。汾酒说,“我是中国白酒产业的奠基者、中华五千年白酒文化的火炬手、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教科书、见证中国白酒发展的活化石”,这依然是软件,是高富帅的顾盼自雄。国窖1573说,“你能听到的历史,135年;你能看到的历史,173年;你能品味的历史,439 年”,这就有点“湿”,引人注目的是,在白酒广告中罕见地采用了第二人称。
在低价位白酒品牌中,湿件似乎更多一点,比如红星二锅头的“年轻就要红”、“把激情燃烧的岁月灌进喉咙”、“将所有一言难尽一饮而尽”道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声,再比如老村长酒的“简单快乐、幸福中国”,“好好生活、天天向上”的质朴表达同样性格鲜明。
总体而言,大多数白酒品牌只想着与经销商代表的渠道资源沟通,在较少的与消费者沟通的场合,往往只是局限在理性层面。很少有消费者会为如汾酒般“大秀肌肉”的表述怦然心动,这就好比我们会由衷地佩服健美运动员肌肉的完美,但在佩服之余,很少会有人真的坠入爱河。没有湿件的白酒品牌只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需要有创意能力,而不仅仅是有分析能力的人来完成这项工作。
“抢劫”一个字或词
白酒品牌要寻找湿件,获取新的基因,往往需要在原品牌名称中加进一个“革命性的字或词”,比如洋河蓝色经典的“蓝”、高沟今世缘的“缘”、汤沟两相和的“和”,江苏白酒目前已占据了这三个字。“孔府家酒,叫人想家”,占了一个“家”字,沱牌舍得占了一个词“智慧”。丰谷特曲“让友情,更有情”,泸州老窖特曲“一生情,一杯酒”,“知心知己,枝江酒”,都想占住“友情”这个词。
“缘”、“和”、“家”、“智慧”、“友情”……这些字或词都深深扎根在民族心理中;既然品牌只存活在消费者脑海里,那么这些字或词就是一个又一个天然的利基市场。占据了这些字或词,就像汽车品牌中的沃尔沃占据了“安全”,宝马占据了“驾驶的乐趣”,才具备成为一个深度品牌的潜质。郎酒占据了一个“郎”字,不假外求,这只能说是天赋异禀,随后发展出品牌“群狼战术”,真正是风行水上,自然天成。
笔者有时觉得,做品牌其实就像“王老虎抢亲”一样抢劫一个字或词,“郎”、“蓝”、“福”原来都是字典里的字,但是郎酒、洋河、金六福分别紧紧地把它们抱在怀里,品牌逐渐有了深度以后,消费者也就相信这个字是他们的。中国字是方块字,一个字就是一个世界。抢到这个字以后,品牌也就具有裂变、内涵扩展的种种可能。除了字以外,慢慢开始抢劫词。海飞丝把“去头屑”三个字紧紧地抱在怀里,中国白酒在黄金十年则流行“大词赶集”,例如,中国梦、中国荣耀、中国品味、中国风景、中国骄傲、中国性格……
“大词赶集”只是一种偷懒,是掩盖创意能力缺失的“吼嗓子”。笔者有时想,为什么不在熟读顾炎武等人历史地理学著作的基础上去寻找差异化呢?为什么不能找到“我之为我”的那一种独特的个性气质之后再与消费者沟通呢?又为什么不用文学的方法去研究消费者呢?中国白酒品牌重塑,必须能够清晰解读西门庆、薛蟠、贾宝玉……的人格类型才会有更多未来的可能。 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 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当时刘备46岁,诸葛亮只有26岁。三国时代的主要人物,曹操年纪最大,生于公元2世纪50年代,刘备生于60年代,周瑜、司马懿生于70年代,孙权、诸葛亮、汉献帝都生于80年代。
白酒行业的重度消费者年龄分布在30至50岁,这20年是一个男人喝酒的黄金年龄,内在的生理条件,外在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正相契合,也就是说当今的60后、70后、80后是白酒行业的重度消费人群。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原因,每一个中国人对1900年前的刘备、周瑜、司马懿、孙权、诸葛亮、汉献帝都了如指掌,对他们一生的行迹、行为模式,甚至心理隐秘都津津乐道,抱有莫大的兴趣。如果白酒的消费者是这些古人,我相信白酒企业的消费者洞察会比现在深入得多。
在白酒行业进入调整期的2013年,我们要像熟悉刘备、周瑜、司马懿、孙权、诸葛亮、汉献帝……那样,熟悉当今60后、70后、80后的白酒重度消费者。如何能做到熟悉,要熟悉到什么程度,笔者的心法是“用文学的方法研究消费者”,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学问能像文学那样如此深入“人性”。杨贵妃不仅身材是丰满的,人物形象、内心世界也是丰满的,这主要得益于《长恨歌》以及许多野史,而不是《新唐书》或《旧唐书》,就像我们对三国人物了如指掌主要得益于《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一样。
“用文学的方法研究消费者”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要追求数量,而要定义出一个又一个人性“个案”。
看着白酒行业黄金十年离去的背影,白酒企业要开始有意识地遏制一种把消费者“总体化”的惯性思维,要把消费者当成是“顾客”。顾客与消费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顾客是“个别的人”,消费者是“大众”,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如何把“个别的人”转化为“有数量意义的市场”,主要的办法是区分出人格类型,比如《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就是12种女性人格。白酒是大众消费品,偶尔“处庙堂之高”,大部分时间“处江湖之远”,通过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研究白酒顾客的人格类型是酒企过冬的一种方便法门。
其次,强调与消费者“同于情”的实证研究。
我们现在所说的“同情”,其意思在古代叫“怜悯”,可怜某某人的意思;古代的“同情”相当于现在的“同于情”,就是与对方处在同一种感情基调、生活场景中,也就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这是公认的“攻心”之法。史玉柱在脑白金上市前,在江阴走村窜巷,与在家闲居的老人抽烟、聊天,就是在做“同于情”的实证研究。黄金十年的盘中盘模式只是一种外在的“暴力与挟持”,是一种意见领袖居高临下的压迫,消费者只好屈从。那是帝国社会“以吏为师”的权利结构,作为权贵阶层的“吏”是权威的来源,也是群体消费、圈子消费的风向标。这种模式会走到尽头,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背道而驰,这也是阿里巴巴的马云反复强调“阿里永远不做帝国”的原因。
在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更多地关注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变迁,走进消费者的内心世界,与他们“同于情”,在理智和情感两个方面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实在是白酒品牌规划的终极心法。是“心法”,不是“手法”,通过挖掘故纸堆,捕风捉影地考证出“我的祖先是某某历史名人”或“我的祖先与某某历史名人说过一句话”,然后作为白酒价格疯涨的理由,而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实际的价值,这是“手法”,手法是靠不住的。
最后,学会用“眼神”和消费者说话。
民国时期,徐志摩和郁达夫都喜欢追求女性。从品牌资产的角度来看,两人旗鼓相当,在杭州念中学时还是同班同学。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留学英美;郁达夫是著名文学家,留学日本。就硬件来说,似乎郁达夫长相上稍逊徐志摩,徐志摩和林徽因一起接待泰戈尔,当时媒体吹捧三人走在一起像极了松竹梅“岁寒三友”,泰戈尔是松,林徽因是梅,徐志摩是竹。徐志摩看上去的确有点瘦,但还没有瘦到竹杆的程度,反正离玉树临风还差一大截。在我看来,郁达夫在情场上不敌徐志摩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郁的性格苦唧唧的,而徐则“神采飞扬”。徐喜欢和小姐、太太们在一起打麻将,有人形容他在麻将桌上的情形是“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大略一方面指其牌技纯熟,另一方面则指其充分发挥“眼神的秒杀功能”。关于“眼神”,曾经见过白立新的《眼神竞争力》,文中他对某酒店服务生的眼神进行了分析:“他的眼神中没有殷勤,也没有歉意,甚至没有专注,他只是把水倒进壶中,完成这份公事而已;他的眼神中也没有热情,甚至没有光,因为他不喜欢这份工作,讨厌我们这些嘻嘻哈哈的顾客”,文章接着分析说:“要创造流连忘返的客户体验,除了用手和用脑,必须要用心”,“而衡量其用心程度的唯一指标,就是眼神。”其实,这只是古老的真理,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毛主席早就说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用文学的方法研究消费者”既是产业观,也是方法论。产业观是指,白酒行业已经发展到需要如此重视消费者价值的阶段,方法论是指“文学的方法”代表着消费者研究的终极视野。身处白酒行业的调整期,企业不仅需要在动作层面加码中低端、争推小瓶酒,更要在战略层面重视消费者,研究消费者。在战略思维上,要从产品价值转向消费者价值,要从厂家思维转向顾客思维,要从统计数据思维转向人性思维、人格思维,要从理性分析思维转向情感创意思维。
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历史的必然性所安排好的任务,将要由个人来完成,或者非其所愿地完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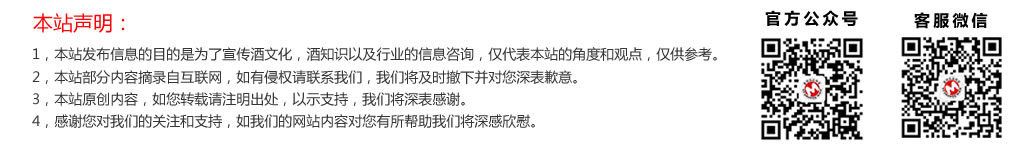 |
| 上一篇: 泸州老窖 融资10亿加码“酒谷”建设 |
| 下一篇: 郑州检察院:不透露房妹父亲案情因怕影响侦查 |
- 相关资讯
- 推荐阅读
- 热点资讯
- 河南永城:打造豫酒品牌样板 全力助推豫酒振兴…2023/04/06
- 河南6个“老金花”如今只剩三朵,3大老牌名酒…2023/04/06
- 2023,豫酒振兴的第二个五年!2023/03/21
- 天明民权葡萄酒精彩亮相亚布力论坛,受众企业家…2023/03/20
- 河南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宝…2023/03/20
- 河南6个“老金花”如今只剩三朵,3大老牌名酒…2023/04/06
- 2023,豫酒振兴的第二个五年!2023/03/21
- 河南一县级酒厂曾名扬四海,后来默默无闻,如今…2023/03/20
- 【豫酒高质量发展大家谈⒁】孙耀州:坚守品质,…2021/06/22
- 白酒行业如何适合网络营销?2021/06/22
- 白酒行业如何适合网络营销?2021/06/22
- 泸州老窖创新表达中国白酒文化2018/12/05
- 【豫酒高质量发展大家谈⒁】孙耀州:坚守品质,…2021/06/22
- 河南一县级酒厂曾名扬四海,后来默默无闻,如今…2023/03/20
- 李嘉诚涉猎BitPay 跟潮流买环亚智富2014/01/06
猜你喜欢
- 限量版红酒让嘉宾流连2014/06/03
- 茅台袁仁国谈白酒行业要仰望星空:…2014/06/07
- 中国企业为何大而不强2013/08/21
- 品鉴进口酒不再进“雾区”2014/03/11
- 武汉女白领KTV里连飙高音 唱破…2014/05/15
- 酒参展,瓶瓶盖盖跟到来2014/03/24
- 不摆酒返礼金是钻“禁酒令”空子2014/03/14
- 全球最著名的十大“奇葩”葡萄酒2016/11/26
- 食品安全宣传周酒类知识公益宣传活…2014/07/20
- 共享世界杯激情董酒邀你猜冠军2014/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