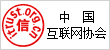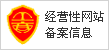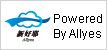周恩来的留东岁月
周恩来在日本名气极大,朝野上下,粉丝众多,历来被视为蒋介石、戴季陶一流的“亲日派”。而这一切盖源于周“人在东京”的一段日子。
1917年9月,从南开学校毕业的周恩来,从同学、师友处筹措了一笔川资,从天津乘船赴日留学,时年19岁。行前,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并写了一首七言诗励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作为江浙人,周恩来与周作人一样,对东瀛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很适应,全无“违和感”。他在当年12月致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日本风俗,不见优美,好在谨言慎行,无不可居之地。倭国虽小,安分克己,尚无不合式也。”为便于饮食,国人咸住中国馆,而周则下宿日馆,住在神田一爿家具店的二楼,“较中馆清静,无喧哗声,便于用功”。10月,入位于神田区仲猿町七番地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参加官费考试。按照当时中日两国政府间协定,中国留学生只要考上东京高等师范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学府,便可享受中国政府的官费待遇,基本衣食无忧。
对周青年来说,在南开学校时,已经学过数理化等课程,且均是英文教材,应问题不大,但来到日本后,则面临如何用日语来表达所学知识的难题。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提高日语水平,以应对官费考试。周恩来每日上课,去青年会阅报,参加同乡和南开校友的聚会,忙得不亦乐乎。在东京,他还重新“发现”了国内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经常从友人处借回去读。翌年1月8日,接堂弟来信,得知淮安的叔父周贻奎在贫病中去世的消息,“哀痛异常,不知所以”。升学的压力,身世的感伤,前途的漂泊不定,周青年的苦闷可想而知。他立志发奋苦读,考取官费。“随后搬到一租金低廉的住处,改包饭为零买,每天废止朝食,以节省开支。”(《周恩来年谱》)
但随着考期的临近,周恩来内心的焦虑与日俱增。他在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而与此同时,他又痛感观察日本社会的必要性:“人要是把精神放在是处,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2月4日日记)
时光如梭。1918年3月4日至6日,东京高等师范入试如期举行,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外加口试。周青年落第。“此后,为准备七月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周恩来年谱》)
其间,周青年曾加入旅日中国留学生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发表了关于“新”的入会演讲,令同胞学子耳目一新。他指出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而“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6月初,“重新开始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准备考试”。7月2日至3日,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入试,日文再次挂科而名落孙山。他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取官文学校,此羞终不可洗。”7月28日,周青年经釜山回天津探亲,9月4日,又回到东京,准备以厉再战。刚好这时,从国内传来母校南开开设大学部,南开毕业生可免试升大学的消息。于是,周青年当即决定调转航向,回国就学。
回头来看,周恩来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介知青,挣扎于对救国道路的摸索和对个人前途的焦虑的夹缝中,所面对的压力和矛盾其实与今天出身于农村或地方小县城,来北上广或国外打拼的80后、90后颇有相似之处。革命与国族的前途固然顶重要,但个人的安身立命却也不是次要问题——不仅不次要,有时还须优先考量。否则一步糗棋,就可能满盘皆输,铸成终生“屌丝化”的大错,岂是闹着玩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百年前“人在东京”的周青年最终其实是做了退而求其次的现实性选择,而今天绝大多数80后、90后们,怕也只有向现实妥协之一途。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经京都踏上归途。在京都小作停留,游览了郊外的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等三首新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在日本接触了河上肇、幸德秋水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刚刚调整了人生目标的周青年,这时对自身前途等问题的思考,已经有种“辩证法”的味道。
国人常为尊者讳,迷信伟人、名人有时到了不惜穿凿附会的程度,其实很可笑,譬如说周恩来是罕见的语言天才,精通四国外语(英法日俄)云云。据历史学者陈明远考证,“周恩来一直没有完全学会日语。后来的外交文献也表明:周恩来并不掌握日语会话。顺便提一句:周恩来的英语可以说是相当棒,但他的法语和俄语水平,也并不是那么非常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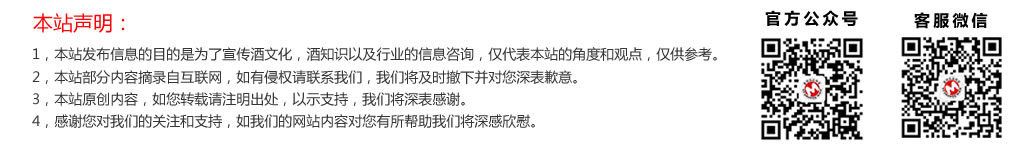 |
| 上一篇: 薛理泰:美中日战略博弈局面或变 |
| 下一篇: 刘强:意大利葡萄酒界的“马可波罗” |
- 相关资讯
- 推荐阅读
- 热点资讯
- 江西四大名酒2021/06/01
- 赤水河,养活了中国60%的名酒,为什么被誉为…2021/05/27
-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想说说豫酒2021/05/16
- 中国白酒之都,年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却只是山…2018/12/05
- 中国八大名酒都有什么?是怎么评比的?2018/12/03
- 赤水河,养活了中国60%的名酒,为什么被誉为…2021/05/27
- 中国白酒之都,年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却只是山…2018/12/05
- 爱上红酒,更爱红酒文化,了解红酒养生2018/12/03
- 中国古代酒具的发展2013/12/23
- 从云集酒坊到会稽山绍兴酒2014/07/26
- 武威葡萄酒文化历史探寻2018/12/03
- 和谐共赢的保健酒企文化2014/06/05
猜你喜欢
- 限量版红酒让嘉宾流连2014/06/03
- 茅台袁仁国谈白酒行业要仰望星空:…2014/06/07
- 中国企业为何大而不强2013/08/21
- 品鉴进口酒不再进“雾区”2014/03/11
- 武汉女白领KTV里连飙高音 唱破…2014/05/15
- 酒参展,瓶瓶盖盖跟到来2014/03/24
- 不摆酒返礼金是钻“禁酒令”空子2014/03/14
- 全球最著名的十大“奇葩”葡萄酒2016/11/26
- 食品安全宣传周酒类知识公益宣传活…2014/07/20
- 共享世界杯激情董酒邀你猜冠军2014/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