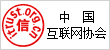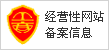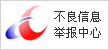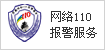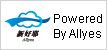三口一杯酒文化饮酒器具饮酒文化源远流长
饮酒器具饮酒文化三口一杯酒文化源远流长
酒,历来是亲人远行,朋友归来之时的必备之品,三杯下肚话匣一开,道声珍重,说声久违,一切尽随那一杯浊酒落入心坎。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中,酒从产生到发
展,衍生了一套套饮酒仪轨,一道道五花八门的酿造工序。酒的酿造与发展最后沉淀积蓄成了一种文化———酒文化。很喜欢湘西鬼才黄永玉的一句话“酒,不可不醉,不可太醉。”说出了饮酒的风范,
也道出了一种人
生———过犹不及。
来到西藏,不尝尝青稞美酒,不经历与人把酒笑谈,西藏之旅总有残缺。在藏
语里,青稞酒叫做
“羌”,如果你对藏民族的音乐有所了解,那一定会注意到,不管哪个地区都有不少酒歌,人们以酒融情也以酒纵情再借酒来表达感情。而在我国古代汉文典籍之中称与藏民族的先民有深厚渊源的西部部落为“羌”,可以说,酒的文化已经融入到了这个民族的血脉里。
青稞酒是以青稞为主材料制成的,逢年过节、结婚、生孩子、迎送亲友的场合里,它的身影必不可少。而在藏民族最重要的节日———藏历新年期间,青稞酒的存在更是贯穿了整个节日,可以说它烘托了节日的气氛,也将千百年的习俗与亲朋之间的感情浓缩于一杯酒之中。
虽然如今的社会,饮酒更多的是用玻璃杯,但在传统文化里或者是武侠故事中,大侠豪客斟上满满一碗酒,豪气吞云地一口而干,摔碗而去的豪迈身影着实影响了不少人。
使得很多人未曾学会饮酒就已经将那份豪迈铭刻在心。而饮青稞酒的器具,虽然没有完全的定式,但大体常见的则有壶、碗、杯等,其中又以杯、碗盛饮为普遍。
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去扎叶巴寺游玩,途经扎叶巴寺下面的村庄时,见一片开阔地上有人群着盛装在活动,打听之下得知是当地村民正在举行开春节的活动,随口问句能参加与否,在村民笑问:“能喝酒不?”爽朗答应可以喝,于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酒舞开始。至今仍记得村民们拿来了陶碗在三口一杯之后开始了畅饮,酒过三巡之后,热情的村民从家里拿出青稞酒,虽然因为酿造的人不同,所喝的青稞甜的、酸的、苦的味道各不相同,但胜在热情、胜在一口到底的豪迈。
在西藏,绿玉酒壶、酒碗、酒杯是珍贵的藏式酒具,畅销于各地。江西景德镇生产的小龙碗,上绘“八吉祥”图案或“六字真言”,也是藏家珍爱的酒具。
诚然,节日里,饮酒是助兴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正如黄永玉所说:“不可不醉,不可太醉。”酒中有文化的传承,酒中亦有一方水土的物产的体现,喝酒的品性更是一方人性格的集中表达。
当酒成为一种文化之后,必然衍生出各种仪轨。
在西藏的饮酒文化中,被广为人知的就是三口一杯了,这是一种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同时亦是一种极具特色的饮酒仪轨。
在古代西藏,吐蕃社会饮酒的多样化,反映了吐蕃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吸收。吐蕃王朝在汲取外来的先进文化方面是十分开放的。据波斯文古籍《世界境域志》载,八世纪拉萨已有西域和波斯、印、缅商人。至于唐朝的手艺人、商贾、学者、僧人等更为数众多。在这样的氛围中,西域的葡萄酒、内地的米酒被作为“时髦”饮料而流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藏区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干寒,除极少数地区可产稻米外,绝大部分地方不产米。吐蕃强大时期占有陇石和川滇的一些地方,有较多的米源,但当吐蕃于九世纪崩溃后,已不能再从这些地方获取稻米。米酒的酿造便难以为继。同样的原因,西藏产葡萄之地不多,葡萄酒自吐蕃失去对西藏的占领后,来源亦日趋减少,自产量十分有限。小麦虽藏区多有栽种,但产量远较青稞为少。这样,以青稞酿酒,便自然而然成为藏族人民普遍采用的制酒方式。青稞酒亦成为藏族酒文化的主载体。青稞酒之于藏民族,既是喜庆的饮料,又是欢乐、幸福、友好的象征,绝非“消愁”之用品。藏族豪放、热情,男女老幼均爱好喝青稞酒。但藏民族也养成了“饮酒有节制”的传统,平时一般是不随便喝酒的,但在喜庆、欢乐的时候,则总是要饮得酣畅尽兴方休。
在藏历新年期间,走在拉萨街头,街头巷尾、大院小屋都散发出浓浓的酒香。青稞酒,不光成了节日的象征,亦是人们祈福新年的一个重要载体,藏历新年初一这天除邻里间“跑切玛”互祝扎西德勒外,一般不出远门拜年,常常是一家人欢聚,品青稞酒,喝酥油茶,话家常。初二起才挨
家去拜访,互道“扎西德
勒”,互敬青稞酒。
在提到藏民族的饮酒仪轨时,就不得不提到俗称“三口一杯”的饮酒方式,三口一杯是藏民族在会客时最主要的一种礼节。客人先用右手无名指沾点酒向空中、半空、地上弹三下,以示敬天、地和祖先(或者敬佛法僧三宝),然后小喝一口,主人把杯子倒满,再喝一口,主人又会把杯子倒满,这样喝完三次,最后把杯子中的酒喝完。对于游人来说,在西藏之旅能得到三口一杯的接待不仅是一种难得的生活体验,更是一种荣耀。
都说藏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而在这歌舞之中也少不了酒的身影,酒过三巡之后,载歌载舞成为了挥洒酒性的重要手段,歌助酒兴,舞借酒力,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在西藏很多地方每年都会举行赛马节,而这时候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如果说马是先民们对于自由的最具体的概念,那么酒就是自由飞翔的翅膀。虽然藏民族几乎家家户户都存有青稞酒也都会酿造青稞酒,但这其中又首推康区,康巴汉子马背上的英姿与纵情歌舞的形象与酒的结合将酒赋予了豪迈的基调。藏民族饮酒与歌舞紧密相连的酒文化这一特色,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酒的存在,贯穿着人类的发展,早在高中历史课本就已经读到,因为人们生产力的提高,粮食的富余,或许是刻意的发明,或许是一个偶然的契机,人们发现粮食经过自然发酵之后,产生的液体原来是如此美味。随着酒的产生与发展,酒的文化也越来越丰富,酒不仅有助于文人借此抒发情怀,也是武将纵马沙场的催化剂。人们饮酒赞酒的时候,总要给所饮的酒起个饶有风趣的雅号或别名。这些名字,大都由一些典故演绎而成,或是根据酒的味道、颜色、功能、作用、浓淡及酿造方法等等而定。
在西藏,关于青稞酒的来历,也有不少神奇的故事。
在西藏民间传说中,酒是从唐代文成公主把汉地酿酒术带到吐蕃时开始的。但考诸史实,藏民族造酒的历史应远比此早。
众所周知,藏民族是古代生息于青藏高原的若干民族和部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藏民族的先民与我国汉文典籍中称为“羌”的民族系统有很深的渊源。羌,意为“西方牧羊人”,原是殷周时中原华夏族人对其西部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落的泛称。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古羌人的最初生息地即在青藏高原,以后逐渐迁徙,分散形成许多的部落,有一部分改为从事农耕生产。古羌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高原文化,据专家考证,早在中原华夏人有麦种之前,古羌人已在高原上成功培育出一种稞麦,即今藏族的主要粮食青稞。因此,酿酒的历史应追溯到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古羌时期。 公元641年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唐蕃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特别是文成公主为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不遗余力,不仅随嫁带去中原各种书籍、食品、工艺品,而且极力协助松赞干布学习先进的唐文化、技术和典章制度,推动吐蕃社会的发展。据藏文史籍记载,公主带去的书中有“六十种讲说工艺技巧的书籍”和“各种食品、饮料配制法”,其中即有造酒的技术。
但是,酿酒是门一复杂的工艺,极不易熟练掌握。酿酒的成败和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操作人员的经验。公主入藏九年后,松赞干布又向唐朝请派“造酒、碾、石岂、纸、墨之匠。”可见当时吐蕃虽已输入内地酿酒法,但尚不能完全掌握。
在藏族古代社会中,并不像现在一样普遍饮青稞酒。在吐蕃王室和贵族中,当时比较盛行饮米酒。这一习尚,很可能是受唐之影响。众所周知,唐代饮米酒之风甚盛,宫廷中更是如此。
一家老少其乐融融地品尝美酒。
满文妍摄敬献美酒。流冰摄收割青稞。赵星摄酒器。赵星摄本报记者赵星/文留香。赵星摄高举欢乐的酒杯,杯中的美酒令人心醉。流冰摄品尝醇厚的青稞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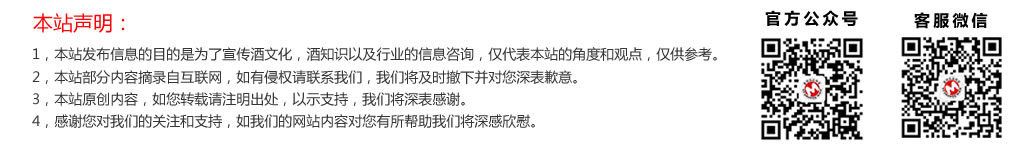 |
| 上一篇: 沉睡中的客家黄酒 |
| 下一篇: 单宁:成就红葡萄酒的幕后推手 |
- 相关资讯
- 推荐阅读
- 热点资讯
- 江西四大名酒2021/06/01
- 赤水河,养活了中国60%的名酒,为什么被誉为…2021/05/27
-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想说说豫酒2021/05/16
- 中国白酒之都,年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却只是山…2018/12/05
- 中国八大名酒都有什么?是怎么评比的?2018/12/03
- 赤水河,养活了中国60%的名酒,为什么被誉为…2021/05/27
- 中国白酒之都,年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却只是山…2018/12/05
- 爱上红酒,更爱红酒文化,了解红酒养生2018/12/03
- 中国古代酒具的发展2013/12/23
- 从云集酒坊到会稽山绍兴酒2014/07/26
- 武威葡萄酒文化历史探寻2018/12/03
- 和谐共赢的保健酒企文化2014/06/05
猜你喜欢
- 限量版红酒让嘉宾流连2014/06/03
- 茅台袁仁国谈白酒行业要仰望星空:…2014/06/07
- 中国企业为何大而不强2013/08/21
- 品鉴进口酒不再进“雾区”2014/03/11
- 武汉女白领KTV里连飙高音 唱破…2014/05/15
- 酒参展,瓶瓶盖盖跟到来2014/03/24
- 不摆酒返礼金是钻“禁酒令”空子2014/03/14
- 全球最著名的十大“奇葩”葡萄酒2016/11/26
- 食品安全宣传周酒类知识公益宣传活…2014/07/20
- 共享世界杯激情董酒邀你猜冠军2014/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