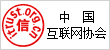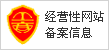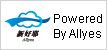世界贸易秩序与我们的无知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一直对中国问题情有独钟。我曾经读过他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该书获得了1994年的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他于2002年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引起了东西方学界的重大辩论。现在我们来通读他的另外一本更加平实的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他的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故事总是让我们会心而笑,他试图跳出西方中心同时也试图跳出民族中心的学术态度,则让我们看到了一名真正的独立学者矢志不渝的学术立场。
在彭慕兰看来,贸易打造的世界,既是一个中间性表述,也是一个历史学表述,既没有对全球贸易化的过度赞美,也不会对此进行过度贬斥。彭慕兰仅仅是陈述了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很早以前,国际贸易就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联结起来,虽然全球化程度在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并非今天才有,所谓的多元世界格局,显然也不是最近才被发现。彭慕兰的工作, 就是想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描述全球彼此相连的关系,过去就存在,现在存在, 将来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余英时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曾经对以西方学术范式为中心的局面深表遗憾。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余先生甚至指出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批判学说”、“解构”之类,以余英时先生的立场来看美国人彭慕兰,发现他们竟然是方法论上的知己。
由此,我对彭慕兰的阅读兴趣大面积高涨。沿着彭慕兰的思考路径说开去,我们就应当建立起一种常识:国家经济必须放在全球背景里去了解,而国家经济和国家体制的差异,正是构成全球环境的主要元素,两者密不可分。国家制度的不同并不是人们拒绝全球贸易的理由,事实上当你拒绝,总有人会推着你往前走。没有一个经济体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置身于全球贸易之外。交流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开放也是一种历史的惯性,那些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制度,那些坐井观天的人们,将为此受到惩罚。
在当下的中国,人们对全球贸易的理解可能是单向度的。要么对全球贸易高唱赞歌,要么抵制;要么认为全球贸易事实上就是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经济运作, 要么把单个民族的贸易问题与主权联系在一起,并以此判定,全球贸易就是一种后现代的帝国主义活动。中国人的如此认知其来有自,主要因素是进入近代史之后,封闭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外力的暴力式推动,导致大多数中国人一方面渴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一方面却又理直气壮的排斥西方技术与国际贸易,一个国家的发展课题由此进入了某种左顾右盼的悖论状态。
事实上,贸易打造的世界是一副饶有趣味的历史图景。沿着彭慕兰的写作路径,我们能够惊讶地发展,至少在15世纪左右,我们的先人在全球贸易上的行为,要比后来此起彼伏的狭隘政策和狭隘心态更开阔,更务实。
那当然是一个令人怀想的白银时代。中国人开始用白银取代日益贬值的纸钞和铜钱,这种特殊的货币政策甚至引起了当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五大洲的居民都受到了深重的影响。中国人将丝织品卖给英国人、荷兰人,后者又以西班牙比索支付。而这些西班牙比索是黑人奴隶在今天的墨西哥、玻利维亚境内铸造的,铸币的原材料则是西班牙殖民当局招募印第安原住民开采出来的。有些白银则是通过西班牙人马尼拉大帆船上的菲律宾人,从墨西哥横越太平洋,直接输入中国。欧洲海盗出没于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中海地区、东非近海。而东非近海也是阿拉伯、印度海盗出没之处,欧洲海盗经常为了保护抢夺到的白银、丝绸、香料,和他们发生火并。
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信徒、基督徒也参与到了全球贸易的秩序之中。他们先后到达也门的红海港口摩卡购买咖啡,导致了白银流入东方。当时,摩卡是全球惟一的咖啡生产中心,垄断咖啡出口贸易长达一百多年。穆斯林信徒在赴麦加朝圣的途中,将喝咖啡的习惯从摩洛哥、埃及传播到了波斯、印度、爪哇和奥斯曼帝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咖啡情有独钟,他在社交沙龙上将这种饮料介绍给当时的天主教贵族。喝咖啡的风气很快在上层社会流传开来,他们用中国瓷器啜饮咖啡,通常还加点糖,而这些糖又来自遥远的非洲大西洋岛屿圣多美岛上的奴隶种植园,或者是巴西的种植园,然后来根维吉尼亚香烟,享受吞云吐雾的美妙体会。有些贵族更爱喝巧克力,英格兰人则渐渐喜欢上了中国茶。巧克力是阿兹特克帝国的贵族饮料,非常珍贵,以致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甚至可以当作货币使用。在西伯利亚,中国茶也可以当货币使用。
我的无知由此凸显。多年来我以为中国人是不懂贸易的,多年来我也以为真正的全球贸易只是一个现代品。由此,我站在贸易无国界的角度,一方面对历史妄自菲薄,一方面对当下的贸易局面张开了热情的双手。这种浅薄的抒情姿态,相比于彭慕兰的理性和独立立场,实在是令人汗颜。
我相信国内如我一样认知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作为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现代中国人,必然或多或少对全球贸易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偏爱,这样的姿态, 源于人们如此热爱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流动,以及经济流动背景下的信息流动,更源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得益于全球贸易的推进,不再仅仅受制于区域经济的画地为牢,更不再受制于官方经济的肆意垄断。
但现在我们要追问!在看到全球贸易的巨大优势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审视全球贸易的负面效应。在另一个向度上,我们也要追问,所谓的全球贸易,究竟是以欧美为核心,还是以每一个国家的主题利益为核心?换句话说,全球贸易真的是如有人所言, 它只是大国之间的游戏吗?只是中产阶级以上人士的游戏吗?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尤其是生活在新科技、新技术之外的人们,他们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享受到全球贸易的好处?
相信很多人只要想到全球贸易, 必然会涌上欧洲中心论的联想。这正是彭慕兰发力之处,也是我们理解这个贸易世界的门槛之一。
身为一个亚洲人, 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扬弃的,就是那种看上去已经成为真理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目的论。这种论调长期以来认为,欧洲才是全球贸易体系的首要推动者,其他地区的人们只做了一些回应的工作。从彭慕兰的文章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国际贸易的确存在太久,欧洲之外的国家和人民一直扮演这重要的角色。欧洲人虽然拥有某种程度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在早期,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法律尚未形成的时代,基本上是依靠暴力或者运气。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摧毁了美洲大陆的原有社会形态,为他们征服大片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他们来到中国打算做生意的时候,贩运过来的商品中, 的确有鸦片这种让人上瘾的食品,而且,在这些食品后面, 则是大英帝国的舰队和大炮。
这的确是早期全球贸易的重要特色之一。今天看起来从善如流的国际贸易体系,其实一直不是一个特别讲究道德的领域,自从它开始的第一天起,奴隶买卖、海上掠夺、贩卖毒品,通常都比生产粮食或者其他基本食品利益更大。这给那些全力抵制全球贸易的人们提供了坚强的口实,封闭的经济、对市场的排斥,对人民的愚弄,对帝国主义的阻击便以一种理所当然的道德力量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政治制度依然专制独裁的国家,这种对全球贸易的抵制竟然成为了当地政府的经济学方法。事实上, 欧洲人和北美人虽然称不上天赋异禀,但也绝不是天性邪恶。我们的目光不仅要对准欧洲与其他地方的贸易,也不仅把目光对准某一地区,而是要放眼多个地区和这些地区之间的互动。世界贸易的创造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共同参与,并不是从头到尾出于同一个经济体或一个国家之手。可以肯定的说, 真正的世界贸易,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与其让我们的情绪停留在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之中,不如更多的关注世界贸易准则的缔造、知识与目标的差异、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文化、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
远在美国的陈志武教授总是喜欢陈述这样的局面:18、19世纪的英国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军队,那个时候,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和陆军加在一起甚至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和陆军的规模,那个时代的国际贸易必须依靠武力来维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的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而一家有远见的中国公司也可以在美国登堂入室。今天的全球贸易的确再也不需要军队支撑了,全球通行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都有了普适性的规则。一个良性的贸易世界正在建立,通过谈判桌取得对方的市场经济认可,比派出一支军队更有效果。这正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她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沟通与妥协、互惠与互利。她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也是正在发展的现实。我们要融入其中,也要时刻审视。这既是一个知识人的学术立场,也是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必要的生活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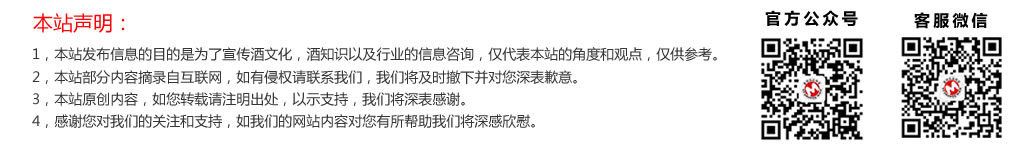 |
| 上一篇: 当前一步:谈华为、海尔的互联网化 |
| 下一篇: 海外反腐:该害怕的是老虎还是苍蝇? |
- 相关资讯
- 推荐阅读
- 热点资讯
- 为何中国的白酒在53度左右?酿酒专家一席话后…2021/06/09
- 你喝的是粮食酒,还是化学酒?2021/05/17
- 中国白酒知识——不同标准分类的白酒文化2018/12/05
- 追溯白酒千年历史:老白干酒曾是白酒代名词2018/12/05
- 身在时尚圈,你真的懂洋酒吗?2018/12/05
- 葡萄酒的5个“隐形杀手”2013/12/13
- 成品酒封装贮存能否终结年份酒乱象?2014/07/26
- 封蜡瓶口是藏酒大忌2014/07/22
- 再论酒类O2O的真假问题2014/07/20
- 如何看待白酒中的塑化剂?2014/07/20
- “酒快到”:9分钟不到延时一秒奖励50元2014/07/23
猜你喜欢
- 限量版红酒让嘉宾流连2014/06/03
- 茅台袁仁国谈白酒行业要仰望星空:…2014/06/07
- 中国企业为何大而不强2013/08/21
- 品鉴进口酒不再进“雾区”2014/03/11
- 武汉女白领KTV里连飙高音 唱破…2014/05/15
- 酒参展,瓶瓶盖盖跟到来2014/03/24
- 不摆酒返礼金是钻“禁酒令”空子2014/03/14
- 全球最著名的十大“奇葩”葡萄酒2016/11/26
- 食品安全宣传周酒类知识公益宣传活…2014/07/20
- 共享世界杯激情董酒邀你猜冠军2014/05/27 >